第一次见到刘沛乔,会对他胸前那条项链印象深刻。那是一条款式较为稀松平常的项链,银白色,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样:“姓名:刘沛乔;性别:男;兵种:侦察步兵;军衔:上等兵……”白炽灯柔和的光线下,项链表面被赋予一种微微反光的质感。 这是刘沛乔在淘宝一比一定制的仿真身份信息牌,“真正的信息牌在退伍时就回收了。”他说,随即又露出一抹笑:“就当是纪念一段往事了。”
那或许是一段大多数人未曾经历的往事——鲜有植被的荒瘠土地,炮火、枪林和弹雨在这里随时可能上演。咧开满嘴獠牙的深褐的非洲狮,被捕食者拧下头颅的黑皮野牛,在沙地上急速奔跑的猎豹……这里是属于动物的天堂,野性的自然和人类的炮火在这里共生。这里是非洲。
从2017年9月暂时放下一纸通知书,应征入伍;到2018年10月响应号召,前往非洲,成为“蓝盔部队”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非洲维和部队的一员;再到2019年3月腿部被流弹打中,回国治疗;最终于2019年9月8号正式退伍。细细算来,刘沛乔已经在部队待了将近两年。
如今,他摘下军帽,回归校园,与大多数华南农业大学学生一样,上课,参与社团,搂着同学的肩膀称“兄弟”,偶尔也会为午饭吃什么而发愁。他似乎与大多数人一样,又似乎不太一样。
“忘不掉,真的忘不掉。”他说。珍藏在宿舍抽屉里的军功章,每逢潮湿天中弹处泛起的痛感,以及无数次午夜梦回间的惊醒,这些都在提醒着刘沛乔——他曾经有过一段出生入死的军旅体验。

命定军旅:与军队的不解之缘
从军,最初来源于一种根植于家族血液里的代代传承。 刘沛乔的老家在湖南娄底,一个土地里流淌着从军血液的地方,母亲是清末湘军掌门人曾国藩亲信将领的后裔。族人多入伍,从火箭空军到武警海军,一种与从军有关的信念内化在家族的血脉之中,世代传承。在军人世家的环境里长大,参军对刘沛乔来说,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从七岁开始,刘沛乔每个寒暑假都会被父母送去表舅所在的部队里,跟着部队战士一起训练。每天6点起床跑4公里,搬着小凳子坐在后排与军人们一起接受思想教育……本该轻松惬意的假期,被响亮的军号声和整齐的踏步声所取代。部队的军人疼惜这个最年幼的孩子,跑步时会故意放慢步伐,等着后边的刘沛乔跟上来。
独特的一年两次的军队体验之旅,不断地塑造着刘沛乔自律的生活方式,也让他愈发明晰了自己的从军之心。中考结束后,刘沛乔便与家人一起制定了从军规划,“高中毕业后考取军校”——在刘家人看来,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计划。然而3年后的高考,刘沛乔却因视力不达标而落选国防科技大学。做完视力矫正手术之后,提前批的军校录取已经结束。 怎么办?刘沛乔毅然下了一个决定:参与大学生征兵,直接进入部队服役。得益于长期锻炼铸就的强健体魄与自己的良好习惯,这一次,刘沛乔顺利通过体检、政审与走访调查,于2017年9月13日正式入伍。
“不是没有想过体验一下大学生活。”刘沛乔说,丰富多彩的象牙塔也曾吸引他的目光,但最终,他选择暂时放下华南农业大学的通知书。“一年后再冲刺只会更难。”
从广州东站到受训的佛山基地,40余公里,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。出发的前一晚,刘沛乔辗转反侧到凌晨三点才睡着。“想着到了部队了要怎么发展,怎么好好表现……”到达基地后,天已经完全黑透了。基地亮起灯,军人们敲锣打鼓,气氛热闹。营区板房的墙上刷了一行鲜明的字体:“欢迎新同志到来!”
18岁的刘沛乔对即将开启的军队生涯充满了忐忑与期待。
辛苦自是不必言说。早六晚十的作息时间,10分钟的吃饭与洗餐具时间,30秒至1分钟的如厕时间限制……在这里,时间被最大程度地分割、量化。进行队列训练时,新兵们的裤缝、两膝处夹满了扑克牌,每张掉落的牌都是“10分钟加训”的惩罚象征。夜里,新兵们在灯下背诵军事理论,以备不时的考察。
雨淋日炙的军队训练里,每周末与父母的10分钟通话成了刘沛乔最期待的事情。“一队人排成长龙,上一个打完10分钟递给下一个,我刚开始每次打都要哭出来……”回忆起两年前的新兵岁月,刘沛乔嘴角抿了抿,不觉露出怀念的笑意。
年少热血:应征前往非洲维和
从小到大,刘沛乔心中都埋藏着一个隐秘的愿望:加入特种部队,去看看真正的战场。 2018年9月,“蓝盔”部队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非洲维和部队来到刘沛乔所在的基地招贤纳才。“去!”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再一次强烈地呼喊起来。揣着一腔热血,刘沛乔顺利通过考核,签下了去往“蓝盔”部队的协议书。“谁也劝不动我。”他说。
与协议书一同写下的,还有一份遗书——加入“蓝盔”部队,就要做好可能回不来的准备。刘沛乔面色平静,写遗书时,手却止不住地颤抖。“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,请告诉我的父母,能加入‘蓝盔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,不要伤心。要让我的妹妹好好学习,要……”
他写不出来太正式、太严肃的“遗书”。如同往常拉家常般,刘沛乔在一笔一划里书写这生离死别之事。 这一年,刘沛乔19岁。 临出发之前,刘沛乔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。他告诉父母,自己将去执行一个秘密计划,一段时间内不能通信。电话里,他语气轻松活泼,还接着父母的话头开了几个玩笑。“其实当时我已经很想哭了。”他没敢告诉家人这个秘密任务的具体内容。
挂断电话,刘沛乔整装心情,踏上了前往非洲的军舰。在大洋上漂了45天后,下船时已是11月的光景。不同于北半球的初冬天气,非洲大陆充满了热烈的阳光,将近30℃的天气让这里看上去充满了盛夏的气息。斑马、大象、奔跑的野牛,动物们生机勃勃而又充满野性。抵达营地后,部队为他们煮了一碗“安心面”,取谐音“安心念”。温热的面汤自食道滑入胃部,妥贴地熨帖着这颗风尘仆仆的心。
但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当晚,第一次袭击发生。
一声巨大的炮鸣声几乎颠碎了所有人的梦境,紧接着是火光。刘沛乔抓起武器跑出帐篷时,战友们已经连发射了两发火箭筒,直接将敌军的卡车掀翻,营地很快又归于平静。刘沛乔望着战友们有条不紊地处理敌军的尸体,“整个人都木了。”
那是一幅太过刺激五感的景象。炮火,死亡,鲜血淋漓的战争。“我就像失了魂一样,感觉这不像是拍电影,又像是在拍电影。”之后的几天里,刘沛乔始终有些紧张。“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况?万一我死了该怎么办?”
许是看出了刘沛乔的紧绷,几天后,连长找到了他,安排他随同其他几位班长一同去支教。非洲的孩子热情好客。“上课前他们专门去打猎、摘果子迎接我们,还送了花环给我。”刘沛乔说。靠着联合国派来的翻译,他和这群黑色皮肤的小孩建立了联系,简单的加减乘除,通用的中文英语,孩子们学得积极又认真。
非洲的儿童多营养不良,每次动身去支教,刘沛乔总会带上一些压缩饼干,有时还会托空运部队的朋友从中国带一些糖果,专门给孩子们尝尝。生活在连天的炮火中,孩子们的笑靥依旧灿烂活泼,刘沛乔紧张的心慢慢松下来。夜幕降临的时候,刘沛乔有时会与当地的居民一起,在非洲舒缓的晚风里燃起篝火,围着火堆唱歌、跳舞。
“可能我无法想象人的声音能传多远,但是我想,如果这些孩子以后能走出非洲的话。”刘沛乔的声音顿了一下,“走到其他的国家,或者走出这个战争世界。他们的人生一定会更出彩。”他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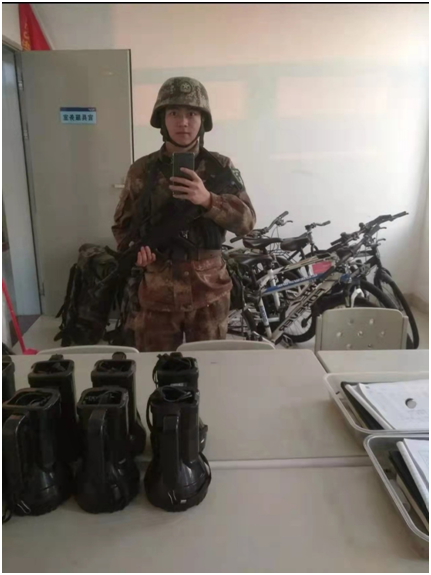
战场硝烟:直面战争残酷
在非洲,刘沛乔曾有三次近距离接触过死神。 第一次发生在某天夜里的巡逻。同往常一样,刘沛乔与战友们列成一小队,沿着营区来回巡逻。按照队列条令,刘沛乔的位置是最后一位。夜色浓重,非洲的夜晚寂寥又寒冷。战士们的鞋底摩擦着沙地,不时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一把枪在这时抵住了刘沛乔的后背。
事后,刘沛乔已经很难再说清楚当时的感受,只记得一身淋漓冷汗,仿佛非洲夜晚的寒气沁入了骨子里。一起巡逻的队友们几乎是在同一时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,迅速将其制服,但仍有一颗子弹射穿了班长的腿部。随后,连长闻讯赶来,将负伤的班长送去野战医院。负责诊治的医生告诉他们:“做好心理准备,他可能要高位截肢。”
连长蹲在地上,忍不住哭出了声。
“那时班长才24、25岁。”刘沛乔的声音低了下去。回国后,他曾经去探望过班长。“比我乐观多了。”他有些自嘲地笑笑,“经常劝我,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”
这很难做到。炮火、枪声都太过鲜明,刘沛乔很难忘记。
最不能忘记的是第二次“死里逃生”的经历。2019年2月,刘沛乔与战友负责护送一批难民前往首都进行政治选举。日头有些毒,刘沛乔与战友们坐在装甲车上,身上将近5千克的装备让人不住冒汗。不出意外的话,他们将于几天后顺利抵达目的地。
突袭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。前路突然炸开,尘土飞扬,先行的装甲车被掀翻。连长一声令下:两辆装甲车护送难民先撤离!随后,观察员带来一个令人心凉的消息:四五公里外,两辆装甲车与两辆满载枪炮弹药的卡车正在步步逼近。
一场混战不可避免。失去装甲车的防护,攻击显得有些单薄无力。刘沛乔与战友们边打边退,不断卸下身上的装备,以减轻负重。身后是追击着的敌人,无数颗子弹划破空气,险些擦过身体。战士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跑!
“两条腿跑了十几公里。”刘沛乔回忆。在敌军的袭击下,刘沛乔和其他9名战友被逼入一栋尚且立着的小建筑,那是一栋三层建筑,在炮火洗礼下只剩最后一层天花板。有了建筑的遮蔽,刘沛乔一行人重新振作起精神。步枪手、狙击手和机枪手,轮流交班进行扫射,护住这座建筑里唯一的两扇门。
带出来的食物和水在第一天就消耗殆尽。为了水,刘沛乔和战友们制作了简易的蒸馏装置,雨水、衣服上的汗液、甚至是尿液……都得进行蒸馏后再利用。令人绝望的是,敌人的援军还在不断增加,从最初的十几人不觉间已增加至三四十人。
“我当时一边哭一边打。”刘沛乔说。“不要死”——这是他当时最大的念头。没有防御任务时,刘沛乔时常靠在角落里发呆,外头枪声不断,恐惧、冰冷袭上心头,攫住他的心脏。
连续两天两夜的死守之后,第三日,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划破清晨的宁静。刘沛乔听到战友欣喜地叫喊:“是援军!有救了……”巨大的惊喜感伴随着疲乏与脱力瞬间袭来,刘沛乔晕了过去。
“感觉像是做了一个梦,很不真实,偏偏手上的输液管又在提醒你,你是真的经历过。”
后面的日子,似乎又回到的原有的轨道:与战友们去巡逻,与非洲居民们一起去打猎……这种日子持续到2019年3月——在一次人质营救任务中,一颗流弹击中了刘沛乔的小腿。这个流弹将他暂时送出军营,也将他送回祖国。
心之所向:部队才是我的归属
父母是在刘沛乔回国后第二天赶来的。为了安抚父母的情绪,刘沛乔撒了谎。“我跟他们说,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摔到了。”父母心疼得掉眼泪,却也夸他是“好样的”。他们此时仍然不知,刘沛乔是在非洲作战时不慎负伤的。
事实是在刘沛乔正式退伍后才“暴露”的。“上周我就被叫回家了,被父母关在家里批了一顿。”刘沛乔说。父母一开始是震怒,随后则是不住地心疼与后怕,高高扬起的巴掌,终究还是舍不得落下。
在各大医院躺了近半年,接受了各种康复训练后,2019年9月,刘沛乔回到华南农业大学,就读于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。他与许多大学生一样,上课,去食堂吃饭,加入社团,参加辩论赛等活动。两年没有接触学业,他坦言自己“压力还是挺大的”。课后,他时常会找老师请教问题。
对于未来,刘沛乔说,他想学成之后去考军队的文职人员。他想,他终究还是离不了军队。 直至今日,刘沛乔时常还是会梦到非洲。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,如同放电影般在梦境里不断盘旋,使他惊醒。这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(PTSD),他无法控制。
“或许可以把项链摘掉?可以避免触物生情。”采访最后,记者提了一个建议。
“我本来就不想忘掉。”刘沛乔咧开嘴,神色里有释然,又带着几分孩子气的骄傲。“你说——有多少人的人生可以拥有这样的经历呢?至少我从未后悔。”
